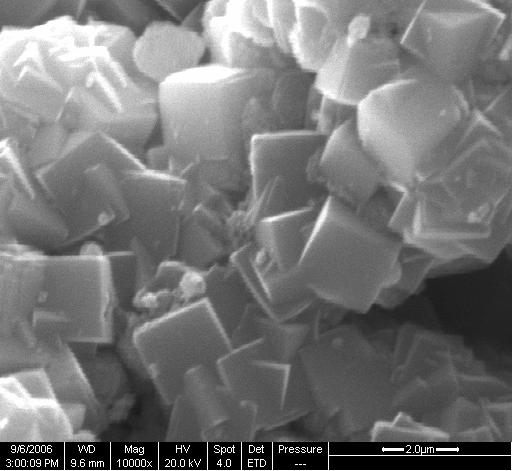鱼与釉,我的高温单色釉艺术折返跑之旅
为了一种釉,也就是这种釉一个很偶然的神奇的效果,为了博物馆的收藏,而这种釉就是原创者都奉劝我收手,上百斤釉,隐灭在几十炉窑火之中,到今天为止,我才只是抓住迷雾中那一点点尾巴。
也许我拽着这个尾巴一点、一点的拉出来,是猫,还是老鼠、或者是大象,甚至一无所有。呵呵,迷雾的尽头,我看不到,甚至想不到。
无间道里头吴镇宇说的,“出来混,迟早要还的”。卖了十多年的陶瓷,终于要搞艺术了,而且是景德镇制瓷历史上的顶尖门类。我已经没有下过一次餐馆了,进过一回超市。每天都是早饭固定三个“烧卖”,中餐,晚餐都在家里吃,小电摩托一圈圈的跑完全镇,请教着每一位老师,看着荷包一点一点的瘪下去,里面每一分钱都省下来投到泥坯,釉剂,以及各种成本之中。
记得,最馋的是,我爱吃鱼,这和我长在长江边有着关系。景德镇新开了一个“诸葛烤鱼”,我咬着牙,一直没有去吃,甚至有一回,走了进去,看见标价58元一份,对着菜单咽了一顿口水,就闪了出来,老婆抱着孩子在门口笑岔了气。搞自己所爱,我不想找家里要,珍惜每一分钱,依靠自己一点积蓄和头脑,去解开色釉的密码。
做这事,好似鲁迅说过“人就像个苍蝇,飞一飞,结果绕了个圈,又落在了原地。”
烧这个釉,一炉、一炉的温度一路小跑上去,一个一个锥倒下去,一段一段、一炉、一炉的测试,每一炉从希望到失望,然后又从希望到失望,最后,又一炉一炉的降温实验,折返跑。结果,后来又发现其他某种因素的影响,又不的不调整后,重新来过一回,温度一段一段冲上去,又一段一段的降下来。就这样,我已经来回跑了5、6趟了。
烧这个釉,厚度一点、一点的增加,一炉一炉的测试,每一炉也是从希望到失望,然后又从希望到失望,最后又不得不一点一点的减下来。折返跑。结果发觉其他的因素的影响,又不得不调整重新一点点的增加、减低。
烧这个釉,升温曲线,烧制的时间,恒温的时间,窑位选择,色剂调配等等,等等。蚊子的叮咬,试片、成品一片一片刻满了我人生的回忆。
还有很多很多,加在一起,又变成了更多的组合,每次面对一堆堆的数据,我抓狂。再烧制下一炉怎么组合,我写这些字的时候都在摇头。
28号,送老婆和孩子回云南去了,赤条条的一人落在景德镇,少了些牵挂。
想起,干这个高温色釉事情,是为了一个朋友的嘱托。我第一次非常失败的交差了,而这位朋友来的时候,东西看都没看,先将成本交给我的手上,说道:“不够,你说话”。当时,我是感动的一塌糊涂。因而我一定要将这个色釉神奇的效果交付与他,不管付出的有多大。
我又想起了,算了,我就别想了。
人的一生奔波并非一定都能达到成功的彼岸,但我们完全可以在努力的过程中,保持一种不败的状态,这也可理解为体验着参与着的状态,至少老了想起时不会回悔我在景德镇的人生。
回首过去,年少往事忘记大半,仅剩碎裂模糊的片断,早已想不起来上学时候老师在全班念我的志愿作文中,自己想做的到底是科学家、老师、工程师......还是平凡的人了。
我的那篇作文中的梦想虽忘了,但到底那是拿来向美丽和严肃的语文老师交差用的。
只是多少年后的某日,景德镇的那间厂房,打开尘封以久的纸箱,看着一张张泛黄的数据和一件件的老物,才发现,原来自己,也在景德镇陶瓷艺术上留下了一笔,许多人、许多事,许多的欢笑、许多的苦恼,还有自己曾有的勇敢和天真 ......(了了亭·李申盛/文)

 会员登录
会员登录